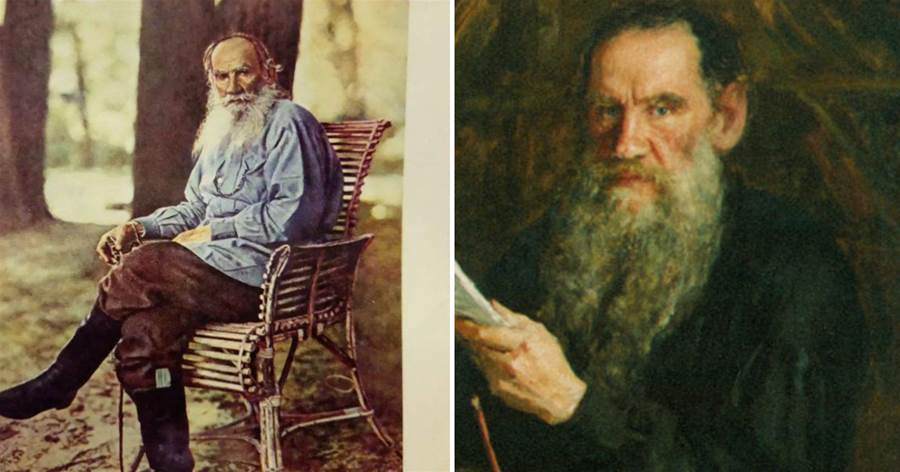1990年底,在《上海文學》做編輯的姚育明收到一封信。
他拆開信,里面還有一篇文章。
信是史鐵生寫的,文章是史鐵生的新作。
文章15000字,姚育明讀完,就知道這是難得的佳作,直接到副主編辦公室,激動地說:
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
周介人看完,直接拍板說:「發,馬上發,明年第一期。」
為了能在1991年1月發表,原本已經準備發的一篇文章,被取而代之。
史鐵生的這篇文章,就是他最美的散文《我與地壇》,按理說,散文不能當做小說發,但是周介人說:
這期的小說分量都不夠,缺少重點稿,你去給史鐵生說一聲,這篇稿作為小說發吧,它內涵很豐富,結構不單一,跟小說一樣的。
在周介人看來,小說的地位比散文重,按照小說發表,對史鐵生來說并不虧,可是史鐵生得知后,卻說「就是散文,不能按照小說發,如果有難處,不發也行。」
文章發表后,讀者一讀,酸甜苦辣的滋味都有了,很多被病痛折磨的人,也覺得找到了安慰,無數煩惱困惑的人,似乎也看見了某個答案,看見了某種希望。
據姚育明說,當時有讀者直接說:1991年整個中國文壇沒有文章,只有《我與地壇》立著。
這話當然有些夸張,但足以說明讀者有多喜歡這篇文章,作家韓少功也說:我以為1991年的小說即使只有他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以說是豐年。
很多年過去了,喜歡《我與地壇》的人依舊很多,失望時,能從里面看見希望之有,恰在與永遠的追求中,迷惘時,能從里面看見,智慧恰在勘破迷惘的途中涌現,痛苦時能從里面讀到人生有無窮的痛苦,所以需要不斷的信仰。

01
史鐵生出生的時候,新中國剛成立兩年,他的童年,正是國家困難時期,青春時代,又是那場席卷全國的文化革命大浪潮。
很多年前,在北京的一個舊胡同里,小小的史鐵生,經常趴在家里的窗戶上,睜大眼睛看著窗外,努力從過往的人群里尋找母親的身影。
父母要出去工作,經常陪著他的,是奶奶,世界給他的第一個回憶,就是躺在奶奶懷里,拼命哭。
奶奶看著哭得厲害的史鐵生說:「你快聽,聽見了嗎?」
正在哭泣的史鐵生,就停止哭泣,窗外就傳來一陣聲音,也許是鴿哨的聲音,也許是秋風的聲音,也許是落葉的聲音,也許是奶奶的哼唱聲。
哄他睡覺的時候,奶奶就唱催眠曲,「麻猴來了我打它……」
後來,奶奶說自己會死,史鐵生就天真地問:
「死了就怎麼了?」
奶奶說,死了就找不到奶奶了。
史鐵生不聽話的時候,她就說「再不聽話,奶奶就死了!」
上學后,史鐵生就是真正的學霸,中學就讀于清華附中,體育課上,跑起步來,是妥妥的運動健將,只要參加比賽,總能獲得名次。
史鐵生最喜歡的是跑步,八十米跨欄跑起來,速度依舊快,那是他的夢想,就是當一個運動員。
十八歲時,史鐵生插隊陜北,身體強健,可是二十歲那年,他卻生了一場大病。
他以為自己身體強健,很快就能熬過去,可是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要讓熱愛跑步的他,永遠站不起來,下半身生活在輪椅上。
他原本想當運動員,可是命運卻要把他往作家的路上引導,要讓他用作家的身份去思考生與死,殘障和愛情,信仰和痛苦。
最終思得,「人所不能,即是殘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也思得因有無盡的痛苦,所以需要無盡的信仰。

02
雙腿癱瘓后,史鐵生陷入了一種可怕的境地,就連在睡夢中,都在大聲呼喚。
那時候的他,甚至對朋友說:「我寧愿拿一只眼換一條腿,再加一條胳膊。」最痛苦的時候,還想自盡。
只能坐在輪椅上,他就暗下決心,「這輩子就在屋里看書,哪兒也不去了」。
可是到了初春,來到院子一看,青天朗照,楊柳和風,史鐵生想,搖著輪椅四處走走,說不定也能重新找到活著的感覺。
最初幾年,他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該干什麼,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他就搖著輪椅,走進地壇,開始在這里思考命運和信仰,殘障和愛情。
他在尋找地壇,地壇也在等他,他會在這里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
「 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從那以后,他就「沒有長久地離開過它」。
每天早上,別人去上班,他就搖著輪椅去地壇,別人在工作,他就在地壇里或思考或看書或發呆,或坐著或躺著。
「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志地想關于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心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
直到有一天,史鐵生豁然開朗:
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史鐵生關于生命的思考,初見深度。
生死斗問題明白了,活著也就不是問題,積極和樂觀,也自然不再是問題。
作家曹文軒說:
《我與地壇》像是與整個人類精神的對話與探尋,字字句句昭示「生命偶然,但不能輕視」這個主題,那些同期作品也揭示了」人生是一個經受磨難的過程」。
但是活著,終究還是要做點什麼,于是,史鐵生走上了寫作之路,曾經想著,要做運動員,可是命運終究讓他成了一名生命的思考者。
從此,他以旁觀者的生命,去看待生命,看待自己,活得清醒而樂觀。

03
人所不能,即是殘障。
殘障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去思考殘障,史鐵生將自己的思考寫下來,一開始,他帶著紙和筆,在地壇里偷偷地寫,有人過來,就合上筆記本,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寫了的東西,也不給別人看,因為擔心最后寫不成,反而落得尷尬。
寫著寫著,居然寫成了,而且還有了一定的名氣,可是史鐵生感覺又不對了,因為他發現,自己整天都在想著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都在想著怎麼找到一個故事,怎麼找到「小說」。
這感覺不對,太不對了。
他覺得自己成了寫作的「人質」,似乎是被逼著寫,還擔心有一天會寫不出來。
史鐵生說:
「 我忽然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質,剛剛有點像個人了卻又過了頭,像個人質,被一個什麼陰謀抓了來當人質,不定哪天被處決,不定哪天就完蛋。」
但是他也明白了:
「只是因為我活著,我才不得不寫作。或者說只是因為你還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寫作。」
一開始,他還在尋找素材,但後來他明白了,「史鐵生」就是素材,而且是一個永遠寫不完的素材,只要能把這個「我」給寫明白了,就夠了。
寫著寫著,史鐵生癱瘓之初的痛苦也沒了,漸漸的就只剩下樂觀。
苦難并不能讓一個靈魂向上的人屈服,命運將他的軀體摁在了輪椅上,可能就是要他的靈魂能夠更加昂揚。
王安憶曾回憶,初次去看史鐵生,還以為史鐵生會抱怨命運對自己的殘忍,會感慨人生的苦難,可是史鐵生一句抱怨也沒有,從頭到尾都在聊餃子。
王安憶說:
史鐵生的樂觀和率真,讓我們這些身體健全的人都自愧不如。
還有有一次,幾個朋友去看他,到了吃飯的時候,大家打算離開,可是史鐵生拉著他們說:
「都別走,我給大家伙兒做飯,做好吃的。」
說著,就擼起袖子開始炒菜,還一邊和大家說說笑笑,他自己倒不覺得,可是朋友們都忍不住流淚了。
命運讓他的身體坐下來,卻讓他的靈魂站起來。

04
地壇之于史鐵生,是他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的逃亡,也是從一個世界向另一個世界的進軍!
在他生活的世界,是殘障,是痛苦,是人的不完美!
而在另一個世界里,是命運,是完美,是愛情,是人的圓滿,是不完美的人對完美的向往和追求!
在地壇里,史鐵生看見了生死,看見了眾生,看見了命運,從而也從有限里看到了無限,從瞬間之中看到了永遠,從人的身上看到了命運的強大。
史鐵生熱愛跑步,最佩服劉易斯,在地壇里,也有一個想靠長跑改變命運的人,每天訓練,總要跑兩萬米。
第一次參加比賽,此人跑了第十五名,可是新聞只宣傳前十名。
他覺得,再努力一點,下一次就可以了。
第二次,他跑了第四名,可新聞上,只有前三名。
第三次,他跑了第七名,新聞上只有前六名。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新聞卻只重點宣傳第一名。
第五年,他終于跑了第一名,可是人家只拍了一張集體照。
後來,這人和史鐵生熟了,在史鐵生面前破口大罵,罵完了,又默默回家,還不忘相互叮囑:「先別去死,再試著活一活看。」
命運要不給你什麼,你再想要也得不到,要給你什麼,也由不得你拒絕。
所謂命運,不過如此。

05
那時候地壇,還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可是後來他發現這個女孩是一個弱智。
這人間的事,也由不得人,任你如何想弄明白,卻終究無法完全弄明白,想著想著,史鐵生也明白了一件事: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說的。
愚蠢和智慧、美好和丑陋,殘障和健全,其實不過是相互完成,僅此而已。
要是沒有愚鈍,機智還有什麼光榮呢?要是沒了丑陋,漂亮又怎麼維系自己的幸運?要是沒有了殘障,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
這就是人世間的差別,差別要有,上帝永遠是對的。
想到這里,史鐵生儼然也成了強者,因為他看見差別的必然,從而也看見了命運的坦然,上天讓他走向殘障,沒有為什麼,這只是一種命運,和完滿健全一樣的命運。
而身處不幸的人,和身處幸運的人一樣,都是在這場人間戲劇里,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般人在做的,要麼慶幸,要麼抱怨,要麼無知無覺地接受,而史鐵生要做的,是「知命」但不認命,他去思考這種命運。
要說命運,史鐵生是真的倒霉,雙腿殘障已經夠痛苦了,可是殘障后沒多少年,兩個腎也出了問題,連尿尿都是問題了,身上不得不插上排尿管,隨身帶著尿壺,還有一身常年不斷的尿騷味。
而那時候,史鐵生還不到三十歲。
這是多大的痛苦,這是多大的折磨,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史鐵生居然寫出了《我與地壇》這樣充滿能量的文章。
腎衰初發的時候,他問醫生:「敝人刑期尚余幾何?」醫生告訴他:「閣下爭取再活十年。」
可是史鐵生卻活了一個又一個十年。2010年12月31日,史鐵生突發腦溢血逝世。
史鐵生去世前,就說要將自己身上能用的器官都捐獻出去,就連身體,也要捐獻出去。
他去世后,人們發現,他身上可以用的器官,只有肝臟和眼角膜,四天后,肝臟成功移植給了一個天津肝病患者身上。
給史鐵生治療過的醫生說:
「史鐵生之后,談生是奢侈,談死是矯情。」
在《我與地壇》里,史鐵生有一句話說:
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
「我常以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為是愚氓舉出了智者。我常以為是懦夫襯照了英雄。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
這話說的不僅是他,也是活在這世上的所有蕓蕓眾生。

06
在《我與地壇》的最后,史鐵生說:
但是太陽,他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當他熄滅著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殘照之際,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燒著爬上山巔布散烈烈朝輝之時。那一天,我也將沉靜著走下山去,扶著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處山洼里,勢必會跑上來一個歡蹦的孩子,抱著他的玩具。
當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嗎?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恒。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
人生就是這樣,苦難也好、幸運也罷、愛也好恨也罷,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如果時間不夠久,還會有一點影響,但若是時間足夠長了,確實都可以忽略不計了。
因為在那無盡的時間背后,所有一切,都只有一個欲望。
在這人間戲劇里,所有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都是你必然的經歷,所有一切都終將消逝,唯有精神永恒。
著名的哲學學者鄧曉芒這樣評論史鐵生:
每個人心靈都有殘障,其實他比我們更健康。
在心靈上,史鐵生確實比我們更健康,我們大多數人,身體是健全的,但心靈是殘障的,但史鐵生身體雖然殘障,但他的心靈,遠比我們健全。
《務虛筆記》出版后,周國平贊賞不已:
在經歷了絕望的掙扎之后,他大難不死,竟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
後來,史鐵生只能靠透析活著,周國平擔心,史鐵生不能繼續寫作了,因為那時候的史鐵生,需要每三天透析一次,一次透析要好幾個小時,三天里,他只有一天稍微有點精神,可是病得那麼嚴重,精神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周國平的擔心,確實是有道理的,但史鐵生卻克服了這種困難,他在這些碎片的時間里,依然繼續寫作,《病隙碎筆》出版之后,周國平一讀,里面沒有抱怨,只有對命運的思考,對人生的思考,對神性和信仰的思考。
周國平說:「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經能夠十分自由地離開肉身,靜觀和俯視塵世的一切。」

07
2018年1月4日,史鐵生誕辰67周年,在一個紀念史鐵生的活動上,70歲的鄧曉芒,拿著講稿站著講了兩個多小時,會場無一人離開,最后他說:
「史鐵生在中國作家中是對哲學問題思考得最全面、最深入的一個,也是以他的文學天賦表現得最生動、最具震撼力的一個。雖然他是不容易讀懂的,但是從未來看,我認為他的作品必將逐漸呈現出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超前性。」
鄧曉芒說得沒錯,史鐵生是不容易讀懂的,他思考神,思考上帝,思考佛陀,也思考殘障,思考限制,思考愛,最終從痛苦里看到愛,從不幸中看到幸運,從現實里看到不公,又從不公之中看到命運,總之,他從人性里看到了神性的光輝。
今天,我們讀史鐵生,到底讀什麼呢?
人生在世,本身就是一種殘障,就是一種受難,無論我們承認不承認,都是如此,在這樣的人生里,史鐵生會告訴我們,苦難并不可怕,殘障并不可怕,愚蠢也不可怕,只要信仰依舊,只要希望還在,只要看破命運殘酷背后的溫柔,就沒有什麼是可怕的。
我們去看史鐵生,不是從別人的不幸上尋找安慰,而是去看到命運,看到曾經有一個智者,不管面對這樣的困難,一直和命運博弈,最終,他從人性里看到了神性,從殘缺里看到了圓滿。
我們看史鐵生,看的是我們自己的命運,只是,史鐵生曾比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命運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