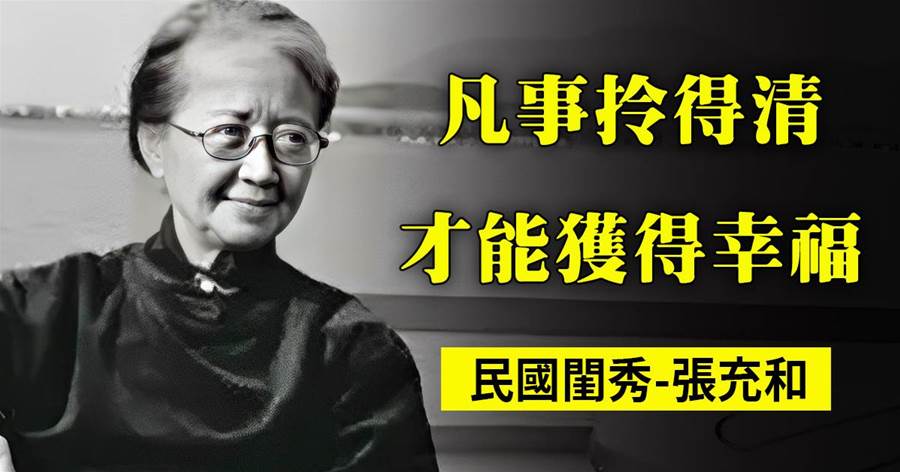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的這首《斷章》短短四句,似乎沒寫什麼,卻似乎什麼都寫了:
那窗,那橋,那柳,還有站在水邊,凝視遠方的人。
有人說,這個「你」,就是民國「最后的才女」——張充和。
在燦若星辰的民國傳奇女子里,張充和似乎并不起眼;
但說起「十分冷淡存知已,一曲微茫度此生」這句詩,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這句詩,是張充和70大壽所寫,也是對她一生的詮釋。
不疾不徐,不遠不近,看得開,放得下,更能拎得清。

張充和出生在合肥名門張家,是「張家四姐妹」中最小的妹妹。

張家四姐妹,前排左一為充和
張家當時有多厲害?曾祖張樹聲曾任直隸、兩江總督、兩江總督,還積極支持洋務運動;
父親張武齡生于清末,是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推動女子教育。
張充和便在這樣一個高貴又開明的家族里誕生。
她既有遺傳自母親的美貌,又有承襲于家族的書香,張充和自幼便出落地十分標致,蕙質蘭心。
吾家有女初長成,十六七的充和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古靈精怪、熱情開朗的性格,令她去到那里都能招來許多追求者。
卞之琳,是其中最為深情的一個。

卞之琳
他們在沈從文的家中相識,張充和是沈從文的妻妹,而卞之琳是沈從文的好友。
「只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顏。夢想著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見,從此我開始孤單思念。」
卞之琳寫給充和的情書多達數百封,每一次見到充和的日子,都被他反復念叨,成了他自己的紀念日。
張曼儀女士編選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卞之琳》所附的《卞之琳年表簡編》中,很多時間線都是這樣的:
某年某月去蘇州探望張充和;
某年某月把某本詩集送給張充和;
某年某月又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
滿滿地都是對張充和的愛。
若是普通女子,就算不愛,也會感動地接受這份感情吧。
但張充和不:「我自始至終對他都沒有興趣,就看見他在那里埋頭作詩,你說我能怎麼辦?」

張充和在沈從文家
不愛就是不愛,就算你追求五年,十年,二十年,還是不能愛。
因為假若勉強接受這份感情,那不但委屈了自己,更是傷害了對方。
事實也證明,充和是聰慧的。
三姐張兆和便是禁不住沈從文的苦苦追求而委屈下嫁,婚姻生活沒有一絲幸福可言;
名媛陸小曼也是被徐志摩的追求所感動,嫁于詩人,最終二人互生嫌隙,再沒有當初的浪漫。
對于愛情,張充和拎得清。
她清楚愛情不是一時感動,飛蛾撲火,而是終身的責任,和永恒的承諾。
愛就愛了,不愛,就不給對方留一絲幻想。
拎得清愛情的女人,才能活得舒服。

說來也奇,卞之琳追求了張充和幾十年,她都沒有同意,原因是:「我喜歡古典文學,但卞寫新體詩。」
但后來,喜愛漢文學的她,竟然與德國人傅漢思結為連理。
1947年,充和在北大開設昆曲和書法課,住在姐夫沈從文家里。
傅漢思是沈從文的朋友,時常到他家請教沈從文。
然而時間一長,沈從文發現,原來醉翁之意不在ㄐ丨ㄡˇ:傅漢思并非為他而來,而是看上了充和。
于是「從那以后,我(傅漢斯)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談話了,馬上就叫張充和,讓我們單獨呆在一起。」
時間長了,就連家里的孩子們都知道了他們的關系,淘氣地喊「四姨傅伯伯」。
一開始,充和只是淡淡笑笑;但沒過多久,她便接受了這份感情,義無反顧嫁給了傅漢思。
1948年,34歲的張充和跟比自己小三歲的傅漢思成婚。

張充和與傅漢思
為什麼拒絕追求幾十年的卞之琳,反而接受了像是不過短短幾個月的老外?
充和是這樣說的:
「漢斯這個人從來就沒有什麼復雜心思,人很老實,也很熱情開朗,是我喜歡的,而且你欺負他,他也不知道。」
充和喜歡和簡單純粹的人在一起,亦如她自己一樣。因為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有趣的靈魂卻萬里挑一。
婚前,她不在意別人的看法,即使被人稱為「老姑娘」,也不會將就地去愛一個人;
婚后,她也不會做攀附于喬木的蘿絲,與丈夫相互獨立,又彼此扶持。

張充和最喜愛的一張照片
這一切,都源自充和清晰的婚姻觀:三觀一致,彼此尊重。
與傅漢思結婚后,他們去了美國。即使生活瑣事不斷,充和依舊沒有放棄事業。
傅漢斯入了耶魯大家教授中國詩詞,張充和去了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書法和昆曲。
他們的生活,就像傅漢思寄出的家書中的一句話:「我們結婚了,非常快樂。」
婚姻中拎得清的女人,過得灑脫又快樂。

愛情上,婚姻中都拎得清的張充和,對于生活更是清醒獨立。
她的精神世界非常豐富,琴棋書畫,幾乎無一不精。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昆曲和書法。
汪曾琪稱贊她的昆曲:「唱得非常講究,運字行腔,精微細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嬌慵醉媚,若不勝情,難可比擬。」

張充和昆曲扮相
章士釗酷愛充和書法,將其譽為「蔡文姬」:「文姬流落干誰事,十八胡笳只自憐。」
才情如此高,相貌如此美,本能與林徽因,陸小曼一樣,叱咤民國風云。
然而,她不屑于在外人面前表現自己的才學,反而是自娛自樂為多。
昆曲,充和多是唱給自己聽:「她們喜歡登台表演,面對觀眾;我卻習慣不受打擾,做自己的事。」
文章,充和多是為抒發情感而寫:「我寫東西就是隨地吐痰,留不住。誰碰上就拿去發表了」。
書法,充和更是沉浸于其中:「 我可以不打扮,也可以沒有金銀珠寶,但筆墨紙硯是我必須要有的,也一定要用最好的。只要有空,我就不得不拿起筆練上一會。」
外表淡薄,內心卻豐盈。
充和曾寫過一首清雅的田園小詩,來抒發自己的心境:
當年還勝到天涯,
今日隨緣遣歲華。
雅俗但求生意足,
鄰翁來賞隔籬瓜。
除卻浮華,回歸本真,這邊是張充和一生的寫照。
她很清楚,所謂表演,那是演給別人看的。你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難免會有取悅他人的意思,真正的趣味就少了很多。
而她要的是生活,琴棋書畫詩ㄐ丨ㄡˇ花,這些不是高高在上的鏡花水月。這些,是生活。
而生活,無需取悅他人,但一定要取悅自己。
拎得清生活的女人,內心富足,心靈充盈。

張充和這一生,在大眾面前十分低調,但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了其芳華。
她曾經得到過很多名人的評價,但最為契合的應該是這一句:
「她是真山真水之間的留白。」
留白,看似無聲,實為大美。
這是充和晚年的好友,美國耶魯大學的旅美作家、批評家蘇煒對其的評價。

晚年張充和
她是如此豐富,卻又是如此簡單。她明明可以光耀一時,去甘愿隱去自己,成為一抹留白。
然而,正如周國平所說: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豐富的安靜。」
「豐富而安靜」的張充和,從來都拎得清:她有清晰的人生道路,不著急,不盲從,靜靜地享受人生蛻變和自我成長。
既讓自己舒服,又讓別人尊重。
愿你也能成為一個拎得清的女人,在人生沉浮中,收獲屬于自己的快樂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