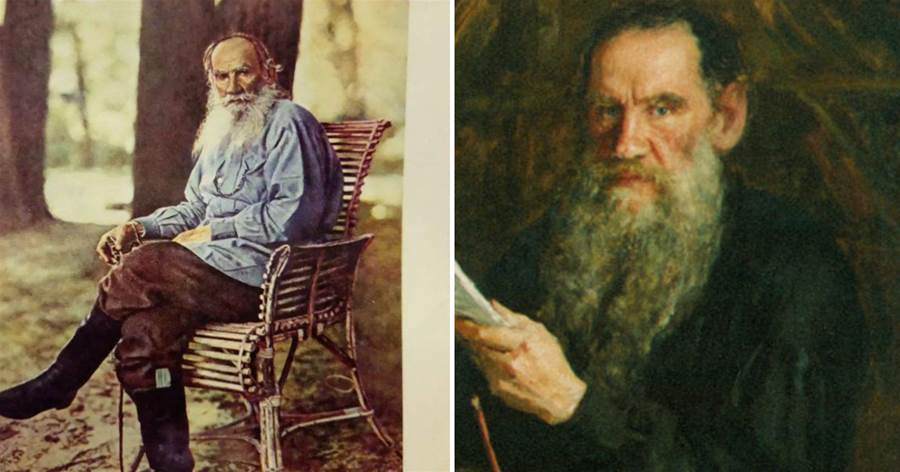27年前上映的《霸王別姬》,堪稱是華語電影的巔峰之作,它集結了當時華語電影界最頂尖的一批人才。
時值陳凱歌導演的創作最佳期,同時,它擁有著頂級的演員陣容:張國榮、張豐毅、鞏俐,連配角都是葛優、英達。
動蕩的年代,悲苦的人間,鳳眼朱唇,胭脂紅淚,亂世里的人情世故在程蝶衣融化了的凄迷妝容里層疊交錯,看癡了戲外的我們。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風雨
清末,山河破碎風飄絮,黎民百姓如同一顆顆棋子,勉力經受著命運的無情玩弄。
那一年,九歲的小豆子被青樓母親切掉了畸形的手指后,進入了戲班學戲。那年頭,戲子是三教九流之輩,可是朝不保夕,胡亂混口飯吃便已知足。
戲班里的孩子們知道小豆子媽媽的身份,起哄嘲笑他,小豆子惱羞成怒,把媽媽留給他的衣服扔進了火盆。
小豆子外表陰柔,骨子里卻還是個鐵骨男兒。
正在這時,小石頭進來了,看到這一幕,心里已明白了幾分。他呵斥了其他孩子,并且邀小豆子跟他一起入睡。
失去了母親庇護的小豆子從小石頭那里得到了溫暖和關照,他分外依戀這位師哥。兒時的那份情意,往往是最真最純,最能貫穿人之一生的。
小石頭知道小豆子不想學戲,有一次趁師父不注意,把小豆子放走了。

同小豆子一起逃跑的還有小癩子,因緣巧合,他們看了《霸王別姬》。看著舞台上兩個角兒,兩人淚流滿面。
抱著「我也要成角兒」的信念,兩人又回到京劇班,一進門就看到眾師兄弟為他們逃跑而集體受罰。
小豆子挺身而出,愿意為自己的逃跑挨打,而小癩子囫圇吞棗地往嘴里塞著冰糖葫蘆兒,而后上吊自盡了。
真是人如鴻毛,命若野草。
吊嗓,練功,挨罰……日子一天天過去,可小豆子的《思凡》總是被他背成「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
」即便處罰,他也執迷不悟。
真是他記不住嗎?不是,小豆子的潛意識里,希望做個真正的男人。似乎,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才能宣泄被迫與自己性別背叛的焦灼和抗拒。

有一次,老闆過來戲班看看有沒有值得投資的人才,輪到小豆子,他還是唱不出「我本是女嬌娥」。
老闆轉身欲走,眼看大好的出頭機會轉瞬即逝,小石頭惱恨之下,拿起水煙袋,下死勁地捅進小豆子嘴里。
一下一下又一下,小豆子既不掙扎也不反抗,鮮血從小豆子的嘴角流出。
突然,他悟了。他嘴角掛著血,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戲詞:「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自此,小豆子的心理性別已經出現了初步的認知障礙。
如果成長要付出代價,這份代價未免也太凄慘。
那一次,小豆子和小石頭第一次登台唱了《霸王別姬》,得到了張公公的賞識。年邁的張公公玷污了小豆子,使得他被迫完成了心理性別由男性到女性的轉變。
事后,小豆子看到井上的棄嬰堅決要撿回來,并取名「小四」。
命運就是這樣,由不得我們安排。我們拼命向前奔跑,所得的并不美好,而失掉的也不少。

感情最怕的,就是錯付深情
若干年后,小豆子已取藝名程蝶衣,小石頭取藝名段小樓,兩人合演的《霸王別姬》名動京師,兩人也大紅大紫。
程蝶衣是一個男旦,在戲中扮演了女人。在生活中,他入戲太深,一時間雌雄不分,真假難辨。
他渴望與段小樓唱一輩子的戲,他發瘋似地喊著:「少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是一輩子!」
段小樓聽完,不過一笑,認為他這是「不瘋魔不成活」。看到蝶衣很生氣,他道了歉,之后照樣快活地去喝他的花酒。

對段小樓而言,唱戲,不過就是一份糊口的工作,怎麼演它都是假的。程蝶衣的那份深情和癡情,他永遠不會懂。
而這,注定了蝶衣的這份情終將錯付。
有天,兩人唱完《霸王別姬》之后,來了個袁四爺。
四爺揮金如土,一出手便是全套珍珠鉆石頭面。他邀請兩位角兒去他家小坐,遭婉拒。
段小樓去青樓喝花酒的時候,救下了菊仙,打算娶她為妻。聽聞消息之后的蝶衣心灰意冷,痛苦不堪,他接受了袁四爺的邀請。
在四爺的宅子里,蝶衣看到了那把年少時許下心愿要送給小樓的劍。一見蝶衣的眼神,四爺便知其意,他把寶劍贈給了蝶衣。
帶著這把寄托著種種復雜情感的寶劍,蝶衣心情沉重地來到段小樓住處,扔給了他。
誰知,小樓竟不認得這是當初自己心心念念想要獲得的寶劍,帶著新婚喜氣的他一臉不以為然:「又不上台,要劍干什麼?」
感情最怕的就是,一個人用盡了真心,每一個相處的片段都刻骨銘心,而另一個卻漫不經心,什麼都忘記。
就像程蝶衣曾問段小樓,還記得第一次登台唱《霸王別姬》是在哪,段小樓絲毫回憶不起來,一旁的那坤卻還記得是在張公公府上的堂會。

一個深情,一個薄情,感情的錯付已是必然。
日寇的鐵蹄踏了進來,在坐著日本軍人的戲院里,蝶衣表演著貴妃醉酒。
忽然,頭頂紛紛揚揚撒下抗日傳單。燈滅,人喧嘩,唯有蝶衣旁若無人地專心演著未完的戲。
混亂之中,只有袁四爺在樓上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蝶衣。兩人都在戲里如癡如醉,恍無他顧。到底,最懂蝶衣的還是四爺。
之后,段小樓被抓,程蝶衣去日本兵營唱昆曲贖人。小樓出來后,蝶衣激動地告訴他日本人也有懂戲的。小樓啐了他一口,他覺得給日本人唱戲便是奇恥大辱。
到底,小樓和蝶衣是兩個世界里的人。
小樓拒絕再與蝶衣唱戲,蝶衣深感絕望,他天天抽大煙,完全不顧熏壞嗓子。後來,是師父用他獨有的方式讓兩人重歸于好。
抗戰結束后,兩人給國民軍唱戲,底下士兵用手電筒亂晃人。段小樓氣不過,與士兵發生了沖突。一片混亂中菊仙流了產。而蝶衣也因曾給日本人唱戲而被抓走。
段小樓竭力求人相救,菊仙也要蝶衣在法庭上說謊茍且保全自身,袁四爺也在法庭上拍案而起,試圖營救,蝶衣卻一心求死,不肯說謊。
之后,他被某高官營救。他的煙抽得更兇了。

任何感情,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終于,時代變了。蝶衣在一次表演中破了嗓,便下狠心戒了毒。
那時,京劇形式有了大變樣,蝶衣很難接受,在一次討論會上他便獨排眾議,堅持「情境」說,反對現代戲,他覺得那不是他心目中的藝術。
可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人人命如螻蟻。
個人于時代,永遠是渺小的。
蝶衣閉門不出,小樓怒斥他:「你一輩子就知道唱戲,你也不出來看看這世上的戲都唱到哪一出了」。
蝶衣不改初衷,幽幽地說:「虞姬她為什麼要死?」
小樓發狠地說了句「不瘋魔不成活」,便離開了。

在段小樓眼中,他這個師弟有點想不開。他從未懂得過蝶衣,他不懂蝶衣對藝術和理想的癡迷和堅持。而真正的愛情和藝術,原本就是這樣瘋魔和執著啊。
蝶衣年少的時候曾撿來一個棄嬰小四,師父死后,蝶衣又收養了他。蝶衣對他像師父一樣嚴格,滿心希望他能繼承京劇的血脈。
誰知養虎為患,小四太吃不起苦了,他只想一步登天成名角兒。
刻苦用功他不會,耍詭計卻比誰都溜。
他使盡手段,挑撥段小樓、程蝶衣和那坤之間的關系,終于,他搶占了虞姬的角色,擠掉了程蝶衣。
蝶衣痛不欲生,從此與小樓絕交。

歷史又來到了一個轉折點。段小樓被小四陷害,并逼迫他誣陷蝶衣,小樓堅決不肯,被拉去欺辱。
歷史有時候真是面照妖鏡,好人是真好,壞人是真壞。
蝶衣來了,他像往常細細地給師哥描著油彩,他們穿著戲服,畫著戲妝,走在街上。戲里戲外,孰真孰假?人生如夢呵。
小樓的心理防線崩潰了,他為了自保,當眾揭發蝶衣是漢奸。他又與菊仙劃清了界限,并說自己并不愛她。
蝶衣和菊仙,都是小樓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緊要關頭,他為了自保,竟統統否定了,拋棄了。
任何感情,都是經不起考驗的。人性本自私,我們以為的不可取代,或許,在某些關鍵時刻都會被輕易抹去。
蝶衣聽后傷心欲絕,滿腔悲憤讓他失去了理智,當眾抖出了菊仙曾在青樓的不堪歷史。
對愛情和人性徹底絕望的菊仙,在雙重打擊之下,萬念俱灰,上吊自盡了。

京戲于蝶衣,是命,于他,卻只是謀生的手段;感情于蝶衣,是執著的夢,于菊仙,是安全感的來源,于袁四爺,是知己般的因緣際會,于他,不過是凡俗人間的一點幸福。
只要受到外界重壓,沒有執念的他自然便選擇放手。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事,是程蝶衣和袁四爺才會干的。而段小樓一生所追求的,不過是如同我們每一個人的凡俗生活,有人問我粥可溫,有人與我立黃昏。

一個人,如何在無常的命運面前保全自己
分離了22年后,兩人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別姬》。台下空寂無人,一束長長的燈光,霸王和虞姬濃墨重彩地出場了,一切恍如隔世。
段小樓讓他再背一次《思凡》,蝶衣脫口而出「我本是男兒身」,一瞬間,他愣住了,他清醒了,他認識到自己是個男人,而不是虞姬。
此生愛上了不該愛的人,錯付深情,不該不該。
一生飄忽而過,成角兒的輝煌,歷史的跌宕;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得到、失去、失而復得;戲、夢、人生……

他抽出段小樓腰間那把劍,如虞姬般架在脖子上,結束了這無法自主亦無法自保的一生。
「霸王是假霸王,可虞姬卻是真虞姬。」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諸位聽得不少。
那些情情義義,恩恩【愛☆愛】,卿卿我我,都瑰麗莫名。
根本不是人間顏色。人間,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臉。」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