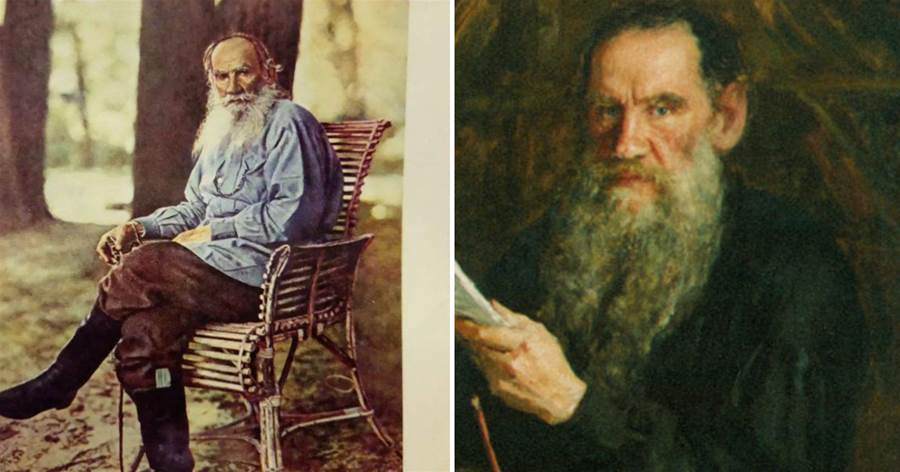最好的閱讀是懷著空白之心去閱讀,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那種閱讀,什麼都不要帶上,這樣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寬廣,如果以先入為主的方式去閱讀,就是挑食似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狹窄起來。
最好的閱讀是懷著空白之心去閱讀,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那種閱讀,什麼都不要帶上,這樣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寬廣,如果以先入為主的方式去閱讀,就是挑食似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狹窄起來。
為什麼不少當時爭議很大的文學作品後來能成為經典,一代代流傳下去?這是因為離開了它所處時代的是是非非,到了後來的讀者和批評家那里,重要的是作品表達了什麼,至于作者是個什麼樣的人不重要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或者過去時代文學作品的時候——比如魯迅的作品時——我們可以懷著一顆空白之心去閱讀,而閱讀當代作品的時候很難懷有這樣的空白之心。
你有你的經驗,你會覺得這部作品寫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經驗,中國很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每個地方的風俗和文化也有差異,每個人的成長環境不一樣以后,年齡不一樣以后,經驗也會不一樣,這會導致帶著過多的自己的經驗去閱讀一部作品,對這部作品的判斷可能會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反過來帶著空白之心去閱讀,就會獲得很多。閱讀最終為了什麼?最終是為了豐富自己,變化自己,而不是為了讓自己原地踏步,始終如此,沒有變化。
無論是讀者、做研究的,還是做評論的,首先要做的是去讀一部作品,而不是去研究一部作品。我上中學的時候,讀的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的,用這種方式的話肯定是把一部作品毀掉了。閱讀首先是感受到了什麼,無論這種感受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欣賞還是不欣賞。讀完以后有感受了,這種感受帶來的是欣賞還是憤怒,都是重要的。然后再去研究為什麼讓我欣賞,為什麼讓我憤怒,為什麼讓我討厭?研究應該是第二步的,應該是在閱讀之后的。
說到寫作時的畫面感,我在寫小說的時候肯定是有的,雖然我不會畫畫,我對繪畫也沒有像對音樂那麼的喜愛。
還有一個原因,相對小說敘述而言,音樂敘述更近一點,兩者都是流動的敘述,或者說是向前推進的敘述。而繪畫也好雕塑也好,繪畫是給你一個平面,雕塑是讓你轉一圈,所以我還是更喜歡音樂。但是小說也好,音樂也好,都是有畫面感的。
我一九九二年底和張藝謀合作做《活著》電影的時候——這片子是一九九三年拍的——他那時候讀了我的一個中篇小說《一九八六年》,
他說我的小說里面全是電影畫面,當時我并沒有覺得我作品里面有那麼多的畫面,但是一個導演這麼說,我就相信了。
至于九十年代寫作的變化,《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為什麼在今天如此受歡迎?昨天張清華還高談闊論分析了一堆理由,聽完我就忘了,沒記住,昨天狀態不好。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覺是這樣,我當時寫《活著》,有些人把《在細雨中呼喊》視為我寫作風格的轉變之作。是,它是已經轉變了,因為它是長篇小說了。但是真正的轉變還是從《活著》開始的,什麼原因?就是換成了一個農民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只能用一種最樸素的語言。

有位出版社的編輯告訴我,她的孩子,十三歲的時候讀了《許三觀賣血記》,喜歡;讀了《活著》還是喜歡;讀到《在細雨中呼喊》就讀不懂了。她問我什麼原因,我想《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受歡迎,尤其是《活著》,可能有這麼個原因,故事是福貴自己來講述的,只能用最為簡單的漢語。我當時用成語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說寫下來沒有一個成語渾身難受,總得用它幾個,就用了家喻戶曉的,所有人都會用的成語。可能就讓大家都看得懂了,人人都看得懂了,從孩子到大人。
我昨天告訴張清華,這兩本書為什麼在今天這麼受歡迎,尤其是《活著》,我覺得唯一的理由就是運氣好,確實是運氣好。
我把話題扯開去,《兄弟》出版那年我去義烏,發現那里有很多「李光頭」。當地的人告訴我,義烏的經濟奇跡起來以后,上海、北京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去調查義烏奇跡,義烏人告訴他們三個字「膽子大」,就是膽子大,創造了義烏的奇跡。所以《活著》為什麼現在受歡迎,也是三個字「運氣好」,沒有別的可以解釋。
《第七天》在一個地方比《活著》受歡迎,就是翻譯成維吾爾文以后,在維族地區很受歡迎,已經印了六次,《活著》只印了三次。在中文世界里,我其他的書不可能超過《活著》,以后也不可能,我這輩子再怎麼寫,把自己往死里寫,也寫不出像《活著》這麼受讀者歡迎的書了,老實坦白,我已經沒有信心了。《活著》擁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當當網有大數據,前些日子他們告訴我,在當當網上購買《活著》的人里面有六成多是九五后。
我為什麼寫《第七天》,這是有延續性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之后,長達十年之后出版的長篇小說是《兄弟》。《兄弟》出版的時候,我在后記里寫得很清楚了,中國人四十年就經歷了西方人四百年的動蕩萬變,這四十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寫作,而且我以后再也不會寫這麼大的作品了,用法語的說法叫「大河小說」或者「全景式的」,他們的評論里幾乎都有大河小說和全景式的,法語世界的讀者對這部小說極其喜愛。
我三十一歲寫完《在細雨中呼喊》,三十二歲寫完《活著》,三十五歲寫完《許三觀賣血記》,四十六歲寫完《兄弟》。
我們這一代作家的經歷比較特殊,我們同時代外國作家的朋友圈不會像我們這麼雜亂。
我二十歲出頭剛開始寫作,在浙江參加筆會時,認識了浙江的作家,當時跟我關系最好的兩個作家,早就不寫作了,都去經商了。我在成長和寫作過程中,不斷認識一些人,這些人一會兒干這個一會兒干那個,他們又會帶來不同的朋友圈,有些人從政,有些人從商,有幾個進了監獄,還在監獄給我打電話,我們在二十多歲時因為文學和藝術走到一起,後來分開了,各走各的路,這樣的經歷讓我到了四五十歲時寫作的欲望變化了,說白了就是想留下一個文學文本之外還想留下一個社會文本。
《兄弟》寫完以后,我覺得不夠,想再寫一個,想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寫一個,于是寫了一部非虛構的書,在台灣出版。寫完這本非虛構的書之后,我還是覺得不夠,中國這三十年來發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太多了,我有個愿望是把它集中寫出來。用什麼方式呢?如果用《兄弟》的方式篇幅比《兄弟》還要長。然后呢,有一天突然靈感光臨了,一個人死了以后接到火葬場的電話,說他火化遲到了。我知道可以寫這本書了,寫一個死者的世界,死者們聚到一起的時候,也把自己在生的世界里的遭遇帶到了一起,這樣就可以用不長的篇幅把很多的故事集中寫出來。
我虛構了一個候燒大廳,死者進去后要拿一個號,坐在那里等待自己的號被叫到,然后起身去火化。窮人擠在塑料椅子里,富人坐在寬敞的沙發區域,這個是我在銀行辦事的經驗,進銀行辦事都要取一個號,拿普通號坐在塑料椅子里,拿VIP號的進入另一個區域,坐在沙發里,那里有茶有咖啡有飲料。我還虛構了一個進口爐子一個國產爐子,進口爐子是燒VIP死者的,國產爐子是燒普通死者的。
昨天晚上收到別人給我發來的一個東西,關于八寶山的,八寶山有兩個公墓,一個是革命公墓,一個是人民公墓,革命公墓里葬的都是干部,人民公墓里葬的都是群眾。那里還真有進口爐子,還是從日本進口的,燒起來沒有煙,全是高級干部在里面燒的。我寫進口爐子時是瞎編的,我不知道有進口的,我沒考察過,沒想到真有。八寶山里面也是有等級制的,夫妻不是同一個級別的不能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不同的墓區。
「死無葬身之地」在我寫「第一天」的時候就出現了,當時我知道這部小說可以寫完了。我現在比較擔心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就是「死無葬身之地」翻譯成其他語言之后不是這樣了,已經不是我們中文里的「死無葬身之地」了。
把社會事件集中起來寫,需要一個角度,這個角度在《第七天》里就是「死無葬身之地」,從一個死者的世界來對應一個活著的世界。假如沒有死無葬身之地的話,這個小說很難寫完,一方面是不知道寫到最后是怎麼回事,有了「死無葬身之地」之后也就有了小說的結尾;另一方面是很多故事可以集中到一起來寫,死者們來到死無葬身之地的時候,也把各自生前的遭遇帶到了一起。
這本書寫了不少現實里發生過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寫作的時候,運用它們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舉個例子,楊飛是去殯儀館以后才意識到自己沒有墓地,那他燒了之后怎麼辦,沒地方放,所以他出來了。路上遇上了鼠妹,然后去了死無葬身之地。還有幾個人也在游蕩,也去了死無葬身之地。所有的人都沒有去過醫院的太平間,只有李月珍和二十七個死去的嬰兒,他們是從太平間去的死無葬身之地。
我還寫了李月珍和那些嬰兒的失蹤之謎,當地政府說他們已經火化了,緊急把別人的骨灰分出來一部分變成他們的骨灰,諸如此類的荒誕事。所以我不能讓他們在太平間里自己坐起來自己走去,這樣寫很不負責任。那時候我想到那麼多年來經常發生的一個事件——地陷,很符合這里的描寫。所以我就讓太平間陷下去,把他們震出來,有震動以后,李月珍帶著這些嬰兒在某種召喚下順理成章地去了死無葬身之地。寫這樣一部小說的時候,事情不是簡單的羅列,什麼地方怎麼處理是非常重要的。寫完《第七天》以后,我覺得夠了,接下來我不想再寫這些了,我應該換換口味了。
《第七天》肯定有遺憾的地方,包括《兄弟》《許三觀賣血記》《活著》和《在細雨中呼喊》都有遺憾的地方,每一部作品我都有遺憾的地方。至于寫錯了和用錯了什麼,就有人認為是硬傷,這個我認為不是那麼回事。當年我寫《活著》的時候,《活著》才十一萬字,里面有個次要人物的名字寫錯了,前面叫這個后面叫那個了,後來是我的一個譯者發現的,他怎麼讀都覺得這兩個人是一個人,就寫信問我,我讀了一下原文,發現確實是一個人,然后改過來了。《許三觀賣血記》要感謝《收獲》的肖元敏,她真是一個好編輯,她在編輯的過程中給我打電話,那時候已經有電話了,她說從敘述上看,《許三觀賣血記》寫的應該是南方的小鎮。我說是南方的小鎮。她說你為什麼不寫「小巷」,寫了「胡同」。我在北京住了很多年了,平時出門都是說什麼胡同,我在寫作的時候都不知不覺寫成了胡同,肖元敏替我把「胡同」改回「小巷」。
如果肖元敏不改回來,肯定又有人說是硬傷了。但是這種問題,并不能用來否定一部作品。因為作家是人,是人都會犯個錯誤什麼的。《兄弟》有五十多萬字,有時候寫著寫著就會犯錯,張清華就找到了一個毛病,小說里面李光頭說林紅是他的夢中情人。張清華很溫和地問我,「文革」的時候會說這樣的話嗎?我說當然不會說,忘了嘛,寫著寫著就忘記了。張清華問我為什麼再版的時候不把它改一下呢?我說沒有必要,假如五十年之后這本書還有人讀的話,根本沒人知道「文革」時候的人不會說這樣的話的,今天在座的同學肯定也不知道那時候不會說這樣的話,如果五十年之后沒有人讀了,我改了也白改。
寫作有時候就是去完成一個過去的愿望。我年輕的時候讀了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說《溫泉旅館》,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里面沒有主角的小說,里面的人物可以說都是配角。看上去《溫泉旅館》是一部傳統小說,它的敘述很規矩,其實不是。傳統小說有個套路,簡單地說就是有主角和配角,但《溫泉旅館》不是,里面人物很多,每個人物的筆墨卻都不多,有的人物好像只有一頁紙就消失了,比如里面寫到一個人,是專門糊窗戶紙的,他糊窗戶紙時跟那些侍女打情罵俏,有個女孩還愛上他了,他揚長而去的時候對那個女孩說,如果你想我了,就把窗戶紙全捅破。《溫泉旅館》對我很有吸引力,我想以后有機會時也應該寫一部沒有主角的小說,大概五六年以后,我寫作《世事如煙》的時候,已經寫了幾頁紙了,小說的主角還沒有在我腦子里出現,我突然想到當初讀完《溫泉旅館》時留給自己的愿望,知道機會來了,于是我寫下了一部沒有主角的小說。
略有遺憾的是《世事如煙》是一部中篇小說,其實我的野心更大,我想寫一部沒有主角的長篇小說,這個機會後來出現過,可是我沒有把握住,就是去年出版的《第七天》,等我意識到這部長篇小說可以寫成沒有主角的小說時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我選擇了第一人稱,已經寫到「第三天」了,「我」和父親的故事已經是主線了,再變換人稱或者角度的話敘述的感覺就會失去。現在看來,楊飛和他的父親的故事還是寫得多了點,我應該寫得少一些,增加其他人物的筆墨,這樣的話這部作品對我來說會更有意思。當然,對讀者來說,他們可能更喜歡閱讀像福貴和許三觀這樣的故事,自始至終的人物命運的故事,讀者能夠很快進入。但是對作家不一樣,他有自己的寫作理想,他想在某部作品中完成某個理想,而這樣的理想往往是他二十多歲甚至十多歲時閱讀經典作家作品時出現的。
我心想以后吧,以后肯定還會有機會。很多讀者熟悉我的長篇小說,但是對我過去的中短篇小說不太了解,他們讀完《第七天》后以為我是第一次寫生死交界的小說,或者說是有關亡靈的小說,我的日文譯者飯塚容告訴我,他在翻譯《第七天》的時候總是想到我過去的《世事如煙》。確實如此,《第七天》可以說是《世事如煙》的某種延續。
如何面對批評?這是作家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我從《兄弟》到《第七天》,被人鋪天蓋地地批評了兩輪,批評對我已經連雨點都不是了,沒有什麼作用了。但是有時候我對批評會有反思,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來批評?尤其從《兄弟》開始,只要我出版一本新書,就會有猛烈的批評光臨。
剛開始可以把它理解為有某種動機,後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雖然批評我的文章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胡扯,但是反過來想一想,贊揚我的文章里胡扯的比例不比這個低。同樣都是胡扯,為什麼贊揚你就覺得不錯,批評你就不能接受?
優秀的文學評論給作家的感受是什麼樣的?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站在這個山頭,那麼他就會在對面的那個山頭;如果我在這個河邊,那他就應該在對面的河邊。作家讀到以后,和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樣,但是又引發了某種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我可以用兩部電影的畫面來向你們解釋,一部電影是安哲羅普洛斯的《永恒的一天》,里面有個人要離開了,他在收拾屋子準備離開的時候,正在放他的音樂。當這個音樂響起來,他家對面窗戶里的某個人也放起同樣的音樂。這個人每次放這個音樂,對面也響起這個音樂,對面那個人是誰他不知道,他們倆都放一樣的音樂。還有一個是我兒子告訴我的,日本的一個動畫片,有一個男孩,可能是經歷過像你們一樣曾經備受摧殘的中學生活,考試考試考試,這個話題可能不適合在大學說,你們現在已經很成熟了,說一說也沒關系。男孩不想活了,走上了自己教室所在的樓頂,準備往下跳的時候發現對面樓頂也有一個學生想往下跳,兩個學生互相看了一會兒,最后決定不跳了。我覺得好的作家看到好的評論,好的評論家看到好的作品的感受就是這樣。
那天的討論會上,張清華以贊揚的口吻說了一句我在北師大的入校儀式上說過的話「我永遠不會放棄對真理的追求」。雖然很矯情,但是他很感動。
我說這句話是有前因后果的,當時我和兒子一起——他高中畢業準備去美國上大學——在家里看了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看完之后我們一起討論,最后的結尾讓妓女替女學生赴死讓我們反感,難道妓女的生命就比女學生低賤?當時我兒子說了一番話讓我很吃驚,孩子的成長讓父母無法預料。他說的是羅素接受英國BBC的采訪,記者最后請他對一千年以后的人說幾句話,有關他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羅素說了兩點,一是關于智慧,二是關于道德。關于一,羅素說不管你是在研究什麼事物,還是在思考任何觀點,只問你自己,事實是什麼,以及這些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麼。永遠不要讓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認為人們相信了會對社會更加有益的東西所影響。只是單單地去審視,什麼才是事實。
當時我兒子基本上把羅素的話復述出來了,我的理解就是永遠不要放棄對真理的追求。當然我兒子的復述比我說得好多了,我這個說得很直白,我的是福貴說的,他的是羅素說的。接著我兒子說張藝謀已經把自己的想法當成真理了,然后說我也到了這個時候,要小心了。確實,當一個人成功以后,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當成真理。那麼真理是什麼呢?我今天不是對在座的老師說,是對你們學生說,真理是什麼,真理不是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你們老師的想法,真理不是名人名言,也不是某種思想,它就是單純的存在,它在某一個地方,你們要去尋找它,它才會出現,你們不去尋找,它就不會出現。或者說有點像燈塔那樣,像飛機航道下面的地面雷達控制站,它并不是讓你們產生一種什麼思想之類的,它能做的就是把你們引向一個正確的方向,當你們去往這個正確的方向時,可以避免觸礁或者空中險情。
真理就是這樣一種單純的存在,你們要去尋找它,它才會有,然后它會引領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