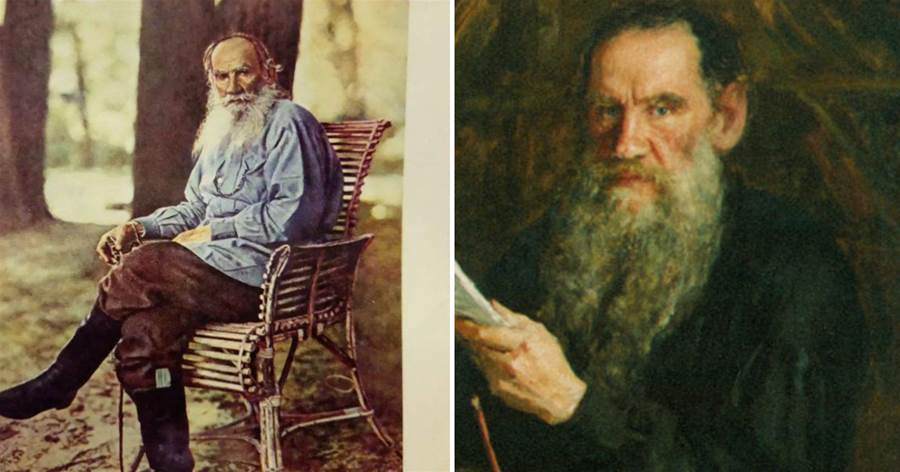有些故事,令人眼紅,可主角卻不能隨意更換。
有些歷史,令人心驚,可身處其中的人,卻無力反抗。
每一個時代的大環境里,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大環境,卻無力主宰這個大環境,他們如同河里的一滴水,構成了河流,卻只能隨波逐流,如同地里的一粒沙,構成了地,卻再也離不開地。
一百年前,中華大地上,戰火紛飛,血肉模糊,人的命運就像暴風雨中的蘆葦,在水深火熱之中,卻無力逃離。
這樣的事情,在今天看來,是歷史,可歷史之中展現的,是人的命運,是在宏大敘事中渺小個體的悲劇,而我們讀歷史,看這些令人落淚的過往,不僅是要銘記,更要看到人的命運。

01
幾年前,紀錄片《二十二》上映的時候,無數觀眾淚目。
這部紀錄片聚焦在戰爭期間被強征為「慰安婦」的22個幸存者的生活現狀,這些耄耋老人,拋開那段歷史,可以平靜地生活,可是那段歷史對于她們的影響,永遠不會像表現出來的那麼平靜。
更可怕的是,《二十二》里的這一群人,還只是多年前那個大環境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電影是人性化的,是人道的,表現了真正的人,對于那殘酷的歷史,就在只言片語之中,更多的是留給沉默,可是國外一位同樣命運的女人——揚·魯夫-奧赫恩——卻將這段隱秘的歷史痛過自述的方式講出來。
她是一個荷蘭人,1923年出生在一個和樂富裕的家庭,有著幸福的童年,她的父母都極具愛心和藝術修養,他們給揚·魯夫播下信仰的種子,讓她在信仰的照耀下成長,從小她就對《圣經》、祈禱和彌撒充滿熱情。
小時候的揚·魯夫,像所有幸福的孩子那樣,覺得母親是無所不能的,要什麼母親都能辦到,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她也迷惑而害怕。
到了16歲,她就長成了一個美麗迷人的大姑娘,在家人及老師的影響下,她決定當一名修女,用一生去敬奉神。
她讀經書: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如果沒有戰爭,一切可能都會朝著夢想的方向前進。
可是在戰爭面前,在不正義面前,在邪惡面前,經書只能安慰有良心的靈魂,卻阻止不了作惡的人繼續作惡。

02
1942年3月1日,揚·魯夫年滿19,日本人入侵了她的家鄉,不久后,她們被抓到集中營。
集中營里,日子很苦,營房內到處都是臭蟲、虱子和蟑螂,更可怕的是,死亡和災難隨時都會降臨,她們就像風中的浮萍,根本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只能將命運交于殘忍的敵人。
有些人攪動著時代的風云,但大部分人只能在時代的漩渦中,隨波逐流,根本改變不了什麼,只能承受,普通人的災難,往往都是無聲的。
在她們這群人里,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但揚·魯夫保持著善良,她盡可能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1944年2月,那天她剛把廁所里面的糞便掏進糞桶抬去倒掉,渾身散發著臭氣回到營房,就被日本人帶走了,一同帶走的,還有9個年輕漂亮的姑娘。
當時她就明白:這絕不是為了某項勞役挑選苦力。
最終,她們被帶到「七海屋」,七個姑娘被留在這里,和集中營的營房比起來,七海屋環境很好,有各種傢俱。
第一天,她們好像被人遺忘了,日本人并沒有出現,可以這反而讓她們更加提心吊膽,因為人家肯定不是放了她們。
第二天,幾個日軍高級軍官出現在她們面前,經過日本人的說明,她們才知道帶她們來七海屋只有一個目的:滿足日本軍官的[性.欲]。
簡而言之,七海屋是一座妓院。日本人警告她們,不要試著逃走,從那一刻起,她們成了日本軍人的性奴隸。
日本人為她們拍照,將她們的照片放在接待區,供日本人選擇。
揚·魯夫向日本人尋求幫助,聲明她們是被迫來到妓院的,可是得到的回應是對方的勃然大怒還和無情地拒絕,沒有得到一絲憐憫。
人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這話有時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大部分人終究反抗不了所在的大環境。
幾百年前,天下還是皇家的,人們賦稅重,苦不堪言,可是由于他們都大環境,大家敢怒不敢言,皇帝換了,大家繼續交稅,這也是大環境。
揚·魯夫生活的大環境,就是一個戰亂的環境,是硝煙四起,日本軍人道德淪喪,所過之處,皆是悲劇。
她一個女子,如何能撼動一個時代?

03
妓院開張的那天,七海屋擠滿了日本軍人,他們[淫.蕩]地笑著,急不可待地盯著這些尚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處女姑娘。
揚·魯夫躲在桌子底下,可是很快就被拽了出去。
她渾身顫抖,尋求基督的幫助,可是這毫無作用,日本軍人依舊毫無憐憫之心地撕開她的衣服,撕開她的身體。
還拿著日本武士刀,從她的喉嚨開始劃過,經過[乳.房],再到腹部,最后到達雙腿。
從那以后,等待她們的,就是接連不斷的日本軍人,一個接一個像潮水一般,流過她的身體,在她的身體上發泄無恥的[性.欲]。
她試著把自己藏起來,可是根本藏無可藏,她偷偷爬到樹頂,被發現之后被毒打一頓。
有一天,揚發現自己可能懷孕了,她陷入更大的絕望,她將自己的情況上報,她一直想獻身宗教,可是一旦懷孕,就全都完了。
她不知道的是,那已經完了。
日本人給她的處理方式,是逼著她吞下一大堆藥片。
後來有一天,日本人暴躁地讓她們收拾行李,她們被送到另一個集中營。

04
離開七海屋之前,日本人對這些受害的姑娘進行訓話,警告她們任何時候也不許將自己的經歷告訴任何一個人,否則就殺死她們。
從那時起,沉默就被強加到這些姑娘的頭上。
離開七海屋后,她們發現同樣遭受迫害的姑娘,很多很多。
離開后,在婦科檢查之中,大量的姑娘患上性病。
後來,戰爭結束了,可噩夢并不會結束,揚·魯夫一直生活在過去的恐懼里,她討厭任何鮮花,因為在七海屋的時候,日本人就是用鮮花給她們起名。
她甚至不敢去看醫生,因為在七海屋,那個日本軍醫無恥地強暴了她,她會深夜做噩夢,醒來大汗淋漓。
她還想繼續做修女,可是神父告訴她,她這樣的情況,已經不適合當修女了。
她不敢將自己可怕的經歷告訴自己的孩子,有好多次,她試圖將自己的經歷告訴女兒,可是最終還是沉默了。
直到1992年,看到電視上不斷出現韓國「慰安婦」悲慘境遇的討論,她才有勇氣將自己的經歷說出。
韓國第一個站出來的「慰安婦」是在什麼情況下挺身而出呢?是在家人全部離世后,不再有家人蒙羞受辱的擔憂之后才站出來的。
有這種經歷的人,都不敢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這是另一個大環境,一個由人性的偏見所組成的大環境。
記得《二十二》當中有一個老人,在被日本人凌辱之后,生下一個孩子,這個孩子長大后,因為有日本血緣關系,一輩子受盡歧視,不能上學,連對象都找不到,他也談過幾個女孩,可是在得知他的情況后,都離開了。
還有很多人,在被日本人殘忍糟蹋之后,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一輩子在孤獨和恐懼之中度過。
戰時,中國慰安婦超過10萬人,相比之下,大多數人都悲劇,連聲音都沒有。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沒有,但命運就是這麼殘酷,這些普通人的悲劇,只能無聲沉默。
曾經,她們在大環境下被逼著接受苦難,如今的大環境,也沒有允許她們將自己的經歷講出來而不受影響。

05
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曾參加過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
可後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里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里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說到底,大家都喜歡昂揚的歷史,喜歡奮斗的影子,喜歡光榮,可是苦難呢?苦難也不是人選擇的呀,那是時代給人的,是命運給人的,是全人類的傷痕。
宏大敘事喜歡忽略個體,但若沒有個體的存在,便不可能有宏大的敘事方式,只不過,個體在大環境之中,是那樣的渺小,是那樣的身不由己,是那樣的無可奈何。
在紀錄片《二十二》中,那些耄耋老人,每天平靜地生活著,像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樣,如果不是某些歷史的痕跡,誰也不會知道她們經歷過怎樣的不幸。
人活著,終究是從過去,走向明天,從一個大環境走向另一個大環境,從一個大敘事走向另一個大敘事。

06
導演郭柯是溫柔的,就像他說的那樣,「我拍的不是慰安婦,是人」。
「慰安婦」是曾經大環境所造就的悲劇,而人,卻是世世代代不斷前行,與命運抗爭,與命運和解,和命運做游戲。
人類,也從一個大環境過度到另一個大環境,每一個大環境中的個體,都有無聲的沉默,有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也許是弱勢群體,也是是看到某些真相而不愿說的,有各種各樣的小人物,他們都聲音沒有人聽,還有很多被大環境不允許的話,也陷入沉默。
而我們能夠從中發現的,就是個人的命運,那麼無常,人所能主宰的,僅僅是能夠主宰的那一部分。
也許哪一天,殘障降臨,也許哪一天疾病降臨,也許哪一天,不可遏制的災難降臨,也許哪一天,大環境突然發生變化,就像到現在還肆虐的疫情,已經改變了很多人都生活,無聲又無力。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在我們的大環境里,前進,前進,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