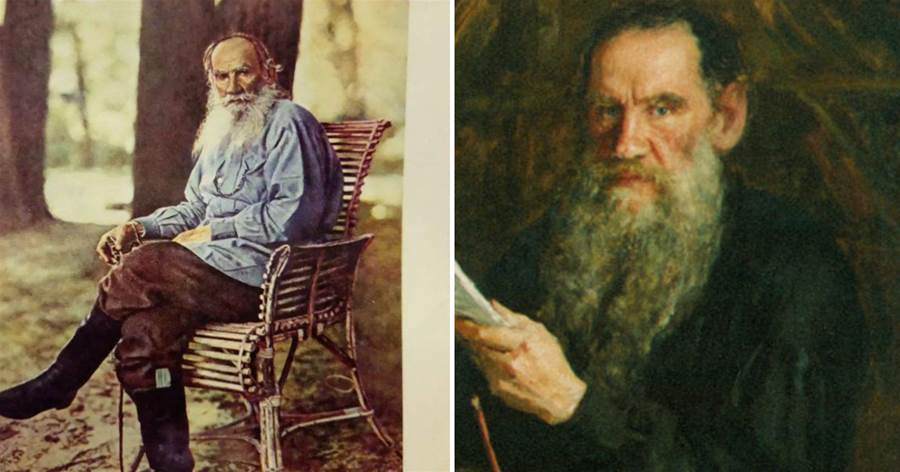卡夫卡在近代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寫出了長篇巨著《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和熱衷于天書寫作的喬伊斯并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與大師。
卡夫卡的作品向來以荒誕著稱,這與他表現主義文學大師的身份密不可分。表現主義提倡書寫個人內在主觀感受,反對直接描寫客觀真實的現實生活。
也正是因此,在卡夫卡的代表作《變形記》中,才會出現主人公格里高爾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只變大版甲蟲這樣完全脫離現實的荒誕情節。

然而,盡管《變形記》向來都以荒誕的外衣示人,但隱藏在背后的現實問題即使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未過時。
在卡夫卡描述的荒誕生活背后,也許有著今天許多人正在經歷的殘酷現實。
《變形記》荒誕在何處?相信絕大多數讀者,甚至沒有讀過,但對情節簡介有一點了解的朋友都會覺得,《變形記》的荒誕之處就在于寫出了人變成甲蟲這種超現實的情節。但實際上,假如個人的眼光僅僅停留于此,很大程度上就浪費了卡夫卡的別有用心。
超自然的情節設置并不是卡夫卡的獨創,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涉及鬼怪的文學作品都有許多。就拿為人熟知的《聊齋志異》舉例,里面的情節哪個不超現實?因此,不能簡單以標志性的「人變甲蟲」作為《變形記》荒誕特色的最大看點。
卡夫卡的突破在于設置了一處強烈的對比,當反常的態度與超現實的情節碰撞后,荒誕的味道便自然散開來了。
在傳統志怪小說中,當人物遇到了牛鬼蛇神,第一反應不是嚇得嗷嗷大叫就是原地發怵,這是情理上的正常反應。
但《變形記》中的人物卻反其道而行之。當格里高爾緩緩醒來,望見自己顫動的爬足時,最擔心的竟然是上班要遲到了,而不是我怎麼變成了一只甲蟲?格里高爾的家人雖然在見到甲蟲真容后也一度嚇得「花容失色」,但卻在平靜下來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按東方的思維理解,此時哪怕是請個江湖騙子來驅走格里高爾身上的妖怪也是正常的。但格里高爾的家人卻始終無動于衷,只是將他鎖在臥室里,這無疑也是十分不符合常理的。

當超出正常認知的場景出現在眼前時,眾人卻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種有悖常理才是《變形記》的荒誕本質。
除此之外,《變形記》的敘述語調也讓這種荒誕感更加強烈。作為第三人稱小說,敘述這一重任由隱身的敘述者來完成。但讀過《變形記》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在敘述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后所發生的一系列荒誕不經的事情時,敘述者的語調始終是平和、冷靜的,仿佛在講述一件十分正常的小事一樣。
敘述語調的克制冷靜無疑更加深了全文的荒誕感,也正是在情節設置和敘述語調的相互作用下,《變形記》才充斥著濃郁的荒誕之味。
然而,荒誕只是特點,探究隱藏在荒誕背后的現實問題,才是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的正確思路。
許多文學評論家認為《變形記》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至上觀念對于個人的壓迫與異化。誠然,在《變形記》中確實有對格里高爾所在公司管理人員無視職員身體健康,將他們當成工作機器對待的情節,也確實多少反映了秉持利益至上原則的資本家對個人的剝削。
但所謂「小說鮮明明地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現代人的共同命運,即無法擺脫蒙受異化之苦的喪失自我的悲哀與尋找「自我」的徒勞掙扎」的論斷其實經不住細細的推敲。

如果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弊端,是個人無法逃脫的命運,那麼格里高爾其實是因無路可走才淪落于此。但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
「別的推銷員生活得像后宮里的貴婦。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領取已到達的訂貨單時,這幫老爺才在吃早飯。我若是對老闆來這一手,我立刻就會被解雇。」
早在小說開頭,卡夫卡便已點明,格里高爾是一個「異類」。同為推銷員,別人可以過著輕松的生活,而格里高爾卻活成了一個社畜。單憑這一點,上述論斷就已全然站不住腳。如果格里高爾自我毀滅的原因在外,那麼活的樂在其中的大多數推銷員又該作何解釋?
也正是因此,我認為與其說是卡夫卡在書寫資本主義的罪行,倒不如說是在鞭笞那些逆來順受的老實人奮起反抗。因為格里高爾變成甲蟲的根源,不在外界,源于自身。
格里高爾遇到的老闆十分苛刻,甚至不允許職員請病假。格里高爾也以「我自己就是老闆的一條狗」來形容自己的悲慘境遇。而且格里高爾完全有跳槽,或者說是反抗的可能,畢竟別的推銷員也活的逍遙自在,完全沒他這麼慘。
但實際上,他是怎麼做的呢?在發現自己變成甲蟲后第一反應是著急下床上班,思考到了公司后怎麼跟老闆解釋。即便後來前往家中看望的老闆秘書見到了變成甲蟲的格里高爾,嚇得落荒而逃時,格里高爾考慮的仍舊是如何能夠攔住秘書,讓公司能夠不把自己開除。可見即便到了這種地步,格里高爾仍舊把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

格里高爾擔心丟掉工作后無法承擔起照料家人義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這種不考慮實際情況,即便錯不在己也把責任大包大攬的行為,卻明顯是病得不輕。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術語,叫幸存者內疚,是指在一場災難中的幸存者可能會在日后產生對不起逝去者的一種心理。這種盲目將責任包在自己身上的特點,無疑也與格里高爾十分相似。
當問題產生時,我們往往不去考慮問題產生的客觀原因,而盲目自信地將一切責任承包在自己身上,這是一種病態的心理。這種想法會導致個人的「自我性」逐漸被消磨,如格里高爾一樣,事事都從別人的角度考慮,而完全不在乎自己。當自我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時,異化變成甲蟲的結局也就早已注定。
十分有趣的是,在當今的社會中存在著許多的格里高爾現象。簡單舉個例子,相信大多數人在學生時代與人發生沖突,受欺負時,都有家長和老師說過,你怎麼不多從自身找找問題?這就是典型的「被動內疚」,有的時候明明是對方故意挑釁,卻要讓被欺負的孩子找自己的問題,孩子上哪找?我弱我就不應該存在嗎?
所以,相比于談論什麼「資本主義異化個人」這種巨觀層面的論斷,我更希望讀者能夠讀出卡夫卡的殷切期盼。不要太過「老好人」,當你都不在乎你自己的時候,還有誰在乎你自己?
而最大的荒誕也莫過于,「我」放棄掙扎,停止反抗,自愿成為了生活的人質。
在閱讀完《變形記》后,我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拼接出了這句話,「
荒誕,也許才是生活的真實底色」。原因無他,卡夫卡所描述的荒誕情節一經細想,反而真實的令人發怵。

在以往的許多研究中,都著重分析了格里高爾一家人態度的前后轉變。父親從始至終都對變成甲蟲親生兒子抱有強烈的反感,而妹妹則從一開始的悉心照料到不耐煩,再到最后號啕大哭要趕走格里高爾。如此比較起來,我反倒對曾經攔住父親,阻止他傷害格里高爾的母親抱有一絲好感。但當我讀到格里高爾死后,三人的臉上不約而同地露出了輕松的笑容時,我僅剩的一點幻想也被徹底擊碎了。
現實往往是殘酷的,對于沒有「自我」,將所有希望寄托于他人的格里高爾來說,親人的接納是他戰勝蟲性,維持人性的關鍵所在。所以,當曾經自己十分寵愛的妹妹說出「他已經不再是格里高爾」之后,格里高爾苦苦維持的人性便徹底消散殆盡,為他人而活的自己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毀滅已成必然。
而如果讀者的想法再大膽一些,荒誕背后的現實也許更加殘酷。
格里高爾家人放棄他的原因在于,他已經變成了一只甲蟲,即「他」已非「本他」。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可以做許多延伸。
當曾經的家人變成植物人,亦或者是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也符合「他」已非「本他」的邏輯?當風光無限的百萬富翁突然家道中落,貧困潦倒,是不是同樣也滿足上述推斷?
于是,我們便不難發現,書中所展現的情境絕非空穴來風,并且還作了一定程度的美化。畢竟當格里高爾的家人難以掩飾自己的厭惡之情,大喊大叫著要趕他走的時候,尚還可以以格里高爾已經變成了一只丑陋的甲蟲,而不再是當初那個活生生的人來做解釋。這種跨越種族的異化,中和了家人的殘酷與冷漠,不至于讓讀者在讀完之后倒吸冷氣。
然而現實生活卻沒有這異樣的美化,向來是以真面目示人。因家人重病而棄置不顧的,絕非沒有。當曾經不可一世的富豪窮途末路,朋友避之不及,嬌妻立刻走人的情景也有很多。在無可解釋的現實中,我們只能直面那些脆弱的關系,那些虛假的情誼,比起小說,殘酷了何止幾倍?
如此看來,我們許多人都曾是格里高爾,只是沒有變成甲蟲。
而之前提到的家人對格里高爾不管不顧,不符情理的情節似乎也得到了「合理」解釋。畢竟在當生母年老便將之活埋的做法都存在的如今,家人變成蟲子后不采取任何積極措施似乎還真不是什麼解釋不了的「荒誕」。

喬斯坦.賈徳曾在《蘇菲的世界》中如此論述荒誕的意義:
「其中的角色時常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非常不真實、像夢一般的情境里。當他們毫不訝異地接受這種情境時,觀眾就不得不訝異這些角色為何不感到訝異。這是卓別林在他的默片中慣用的手法。
這些默片中的戲劇效果經常來自于卓別林默默地接受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荒謬事情。這使得觀眾不得不檢討自己,追求更真實的事物。」
而卡夫卡所帶給我們的,無疑也是同樣的東西。面對這無限逼近現實的荒誕,我們不得不去反思檢討,重新找回生活原本的「真實」。